詹妮弗·潘的新书展示了中共如何以「消除贫困」为藉口,利用其「低保」这一民生保障工程进一步监视政治和宗教异见人士。
作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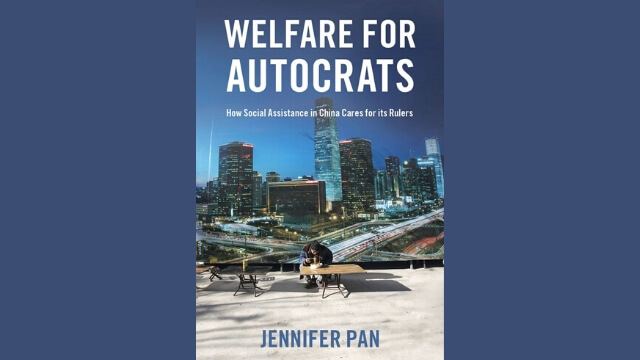
中国福利的失败
《独裁者的福利: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如何为统治者服务》(「Welfare for Autocrats: How Social Assistance in China Care for Its Ruler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是一本出色、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类书籍。读者不会预料到会在此书中看到关於宗教的内容,但其实是有的,而且并非不重要。
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助理教授詹妮弗·潘(Jennifer Pan)的这本书对中国「低保」制度进行了研究,该制度被标榜为「世界最大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也是旨在「消除贫困」的两大中国福利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特困人员救助计划,但是近年来,特困的重要性降低了,而低保的重要性却有所提高。
中国的统计数据总是强调对穷人的照顾,但却暴露出一个严重不平等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了,但全国「城市失业工人却多达6000万人」。到2015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增至41%,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份额降到15%。」中国的宣传可以反驳美国有同样的数据,但是美国并没有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或平等主义国家。
詹妮弗·潘说,中国的「福利制度加剧了贫富分化,而不是缩小了贫富差距」。富人和腐败阶层操控这些制度的手法变得非常娴熟。
低保登场
中共推出低保制度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手段,1993年6月在上海首先试行。1997年9月2日,城市低保在全国推行;2007年7月,农村低保在全国推行。2003年,居民领取城市低保达到高峰,共有2250万人,而领取农村低保的居民竟达5390万人。後来这些数字有所下滑,2017年领取城市低保的下降到1260万人,领取农村低保的下降到4050万人(相比之下,领取低保的特困户总共才470万)。
低保与最近在意大利推出的有争议的「全民基本收入」(reddito di cittadinanza)相似。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现金。问题是,如何确认这些人「无法工作」。
詹妮弗·潘解释道,在中国,「无法工作」的人分为两类。属於第一类的人由於个人残疾或就业市场的问题而无法工作。但属於第二类的人却是因为中共宁愿他们不工作,并要求他们待在家里接受「再教育」。这只是中共所谓的「目标类别」的其中一部分。「目标类别」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来的说法,官方公布了一份「目标类别」名单,并将「涉嫌参与邪教(遭查禁的宗教团体)、宗派、会道门或非法宗教活动」等列入其中。
在家接受再教育
詹妮弗·潘说,1999年法轮功组织示威抗议後,低保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中共最明显的反应是「重拳出击」,包括「大规模抓捕、关押和处决(示威者)」,但法轮功其实「已经改变了中共维稳」的方式。中共意识到,「重拳出击」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法轮功抗议事件後,中共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改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重拳出击」,二是詹妮弗·潘所说的「将安全系统『渗透』到文化、教育和福利中去」。
詹妮弗·潘认为,有一个普遍的错误观念就是,中国的「再教育」只发生在教育转化营、监狱这类机构里。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是在家接受「再教育」的。「由居委会工作人员、楼长、当地警员、社区观察志愿者以及社区一级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干部组成的再教育队不定期上门拜访这些家庭,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回访再教育对象。」接受再教育的人花了太多时间接受再教育,以致他们无法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中共也认为让他们去上班并非是个好主意,他们很有可能在单位「腐化」其他人。所以这类人可以领低保。
若要领低保,就要接受更严密的监视,事无钜细地汇报个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以发放福利的名义实施监视不会那麽引人耳目」,而且「监视、义务、依赖」三角关系也因此得以形成。依中国人的心态,领取低保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觉得自己有义务配合当地给他们发钱的政府人员的工作。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名字会在社区公开,邻里们都希望他们作为低保发放的对象能有忠心的表现。詹妮弗·潘指出,最後,他们领到手的这点钱不足以让他们随意采取行动反对中共,但已足以让他们觉得自己得「依赖」中共。
低保沦为镇压遭查禁宗教的工具
詹妮弗·潘在中国实地考察并记录了低保的运作方式,发现低保常常涉及宗教信仰,这也许令她感到有点意外。她讲述了来自陕西西安的赵先生一家的遭遇。在岳母经诊断患有癌症之前,赵是一位对宗教信仰不太感兴趣的工程师,但因岳母的病,他与被定为「邪教」的门徒会的信徒一起祷告,最後他岳母的病治好了,全家人於2012年加入门徒会。
这一家人接下来的遭遇展示了中共是如何将「重拳出击」与各种形式的维稳手段相结合的。赵先生被抓坐牢,关进教育转化营。他的亲属却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们遭到监视,被安排参加一个与低保绑定的在家接受再教育的计划。詹妮弗·潘采访了一名姓杨的楼长,她负责给赵家发放低保。她坦言承认,她的工作目的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将这家人从「危险的信仰」中「拯救出来」,如果赵家人答应放弃祷告和其他宗教活动,就提高他们的福利发放标准。
还有一类属於用低保绑定在家接受再教育的人,包括那些被抓捕後来获释但当局认为他们接受的再教育尚未结束的人。詹妮弗·潘遇到的两名领取低保的法轮功成员就属於这种情况。他们也许不仅没有被再教育完全转化,反而「表现得极度恐惧,非常希望能摆脱政府的监视」。
简而言之,低保已逐渐成为「镇压和监视的工具」,「一种维护政权的工具,不是照顾百姓,而是照顾中国的统治者」。
中共面临的一些问题
低保的「硬性救助」并非没有问题。首先是费用高,中国的财富也不是取之不尽的。主要为了监视「目标类别」的群体以及支持在家再教育,其结果意味着,领取低保的这些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而那些由於非政治原因应该领取低保(即真正的穷人)实际却没领取到的人的数量将越来越多。这样会导致抗议,可能威胁到低保的政治用途原本要维护的稳定。
但是,中共并不担心这种「强烈反对」。总体而言,中共不喜欢人们抗议,但它认为经济抗议没有呼吁民主或宗教自由的抗议那麽危险。
最後,詹妮弗·潘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共在中国安装了3亿个监控摄像头,已达到了创纪录数量,社会信用体系和高科技保证了全天候监视全世界人民,那麽2020年还需不需要保留低保的政治用途呢?詹妮弗·潘的回答与一些批评中共的人不同:中共知道高科技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她提到,例如,警察数据库(PoliceNet)并非没有漏洞,也并非所有犯罪行为都记录在上面。对於所有的科技反乌托邦,中共非常清楚高科技永远无法完全取代逐人逐户的人工监视。因此詹妮弗·潘认为,在家接受再教育的计划以及利用低保达到监视目的还将继续下去。
西方的监视专家可能会认为,这种高科技监控与人工监视相结合的庞大网络风险(後者主要基於间谍和干预)导致出现大量的「假阳性」(即被划为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而实际上对其无害的民众)。然而,詹妮弗·潘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制度都应在「精准」(将假阳性的机率降到最低)和「联想」(将假阴性的机率降到最低,在本文所述的案例中,指的是那些可能对中共确实构成威胁却未被发现的人)之间进行选择。她说,在新疆,千千万万的维族人和其他丝毫没有做过「对中共政权有任何威胁的人」仍然被关押在教育转化营里,这证明习近平领导的中共选择的模式是「联想」而非「精准」。用一句非技术的术语来说,中共宁可错将数百万无辜者关进监狱,也不放过一个罪犯(即反对中共政权的人)。
来源:《寒冬》